1701101335
1701101336
8)眼科
1701101337
1701101338
关于印度眼科知识传播中国一事,见说于多种医史论著中。所言基本上是围绕着唐代曾有印度僧人以金针疗内障;书目中载有《龙树眼论》,并可见冠有龙木之名的《葆光道人眼科龙木集》、《秘传眼科龙木论》等书流传。然因这些著作的内容显系“中西合璧”,而我们对印度眼科又不甚了解,故无从考究影响之所在。然而如果通晓《妙文集》中“眼科十九章”的内容,则使探究具体影响成为可能。
1701101339
1701101340
首先,在形态学方面中印均有“五轮”之说。由于见于中医眼科专著中的五轮说多依五行立论,故一般认为这是“中医眼科在唐末至宋代理论上的新总结,并非舶自印度眼医”〔34〕;“是由五行说衍化而来”〔35〕;甚或以此作为考证眼科著作内容源流的依据,即凡见此说却又冠以龙木之名者,即可认定是中印“合璧”、“非印著”〔36〕。应该看到,在考察五轮之说的源流时有两点须加注意:其一,五轮之“轮”——“mandla”乃极具印度传统文化特色之词,其本义为圆、球,汉译为“轮”;其哲学性含义为物体的集合、世界图像(汉译“杂色”、“曼荼罗”),这显然也与“眼根”——视觉有直接关系;其宗教性含义指佛与菩萨的聚集之处(意译“轮圆具足”)。其二,中医眼科虽以“五轮”之说为最重要的基础理论,但成立甚晚,且可见逐步改造完善的明显迹象。如传世的《葆光道人眼科龙木集》中说:“又曰目中有五轮,夫五轮者,有风轮、有血轮、有气轮、有水轮、有肉轮。”但又说风轮是“虽有其名,而形状难晓”;血轮亦未定义为两眦,只是说属心、属血、赤黑色是也。附录此书的明刊《龙木集》亦说“肝主风轮在内无形;眼中白翳有小赤脉是血轮主属心”〔37〕。与五行、五脏配合完璧的五轮说始见于托名孙思邈的《银海精微》〔38〕及明清时期的各种眼科著作中。但《银海精微》中有见于金代医家刘完素所创制的著名方剂“双解散”,又可见“予曰:孙真人云如何如何”,显然成书甚晚。要之,中医眼科构建与五行、脏腑相配的五轮说是在宋元间流传的多种不著撰者的“龙木眼科”之后,或亦可说是据此加以改造而成。
1701101341
1701101342
其次是治疗方法。印度眼科在视觉疾患方面主要是从晶状体等“四膜”健康与否来考虑,其结果自然是长于外治(包括拨内障法的产生),但在其他原因(如眼底疾患等)造成的视觉障碍方面则一筹莫展,只能归之于超自然的病因。与之相较,中医在视觉疾患方面多从脏腑功能着眼,故同样是在对视觉生理、病理不具全面之科学认识的时代,前者(印度)转向超自然的解释而归于“不治”;后者则建立起基于脏腑功能的治疗方法。此乃两种眼科知识体系的短长、特点所在。在印度眼科传入后,中医除接受了针拨内障术外,还在钩、割、烙等手术疗法方面大受影响。各书所见钩割之法基本与前述印度眼科的手术疗法相同,特别是火烙用途的解释,与前引“以火烧之,病不会复发”完全一致。如《银海精微》卷上“胬肉攀眼”中云:“剪毕头处用火烙之使其再不复生”〔39〕;《审视瑶函》言:“割之必用烙以断之,否则不久复生”;《目经大成》云:“割如再长,务火烙以断之始平”〔40〕。
1701101343
1701101344
可以说经过在手术疗法上取长补短,中医眼科始见较明显的发展,形成了药物(内治与外治)与手术并重的格局。药物治疗,历来是中医的长处所在,唯在外用眼药方面可能吸收了一些印度眼科的方药〔41〕,但却很难确指何系传统、何为外来。
1701101345
1701101346
在病名方面很难说是否直接受到印度眼医的影响,当时“皆言眼疾有七十二般”,但“及问其数,名迹难言一半”〔42〕。《龙木眼论》的这种说法,或许会对眼病的区别、病名数量的增加产生某种间接的刺激作用,但更主要的是由于接受了拨内障与钩、割、烙等手术疗法,自然会在病变区别上同时受到影响,种种过去没有的内障、外障病名因之出现,用以区分症状特点与治疗方法。
1701101347
1701101348
从流传的眼科著作中,虽能看到印度眼科种种直接与间接的影响,但均系经过改造后的吸收。冠有龙木之名的眼科著作,皆非译作。可以看出医学知识的传播与佛教译经不同,或许主要是以口传身授为主。再者,愿将某种知识说成是本民族所固有的心态在当时也是存在的。例如《目经大成》论“钩割针烙”时说:“原夫钩、割、针、烙之术,仿黄帝九针所作,闻自汉·华元化(即华佗)先生得来,一云龙树山人,未知孰是”〔43〕;《审视瑶函》在详述拨障方法后明记:“右龙木论金针开内障大法”,却又说:“钩割针烙之法,肇自华佗”,“针非砭针之针,乃针拨瞳神之针”。此外还有一类根本不接受手术疗法的著作,如《一草亭目科全书》、《异授眼科》、《银海指南》等。民国时期曹柄章(1877~1956年)在编辑《中国医学大成》时,于眼科唯收此三书。若不是为了满足维系民族文化纯洁的心理需求,则是由于认为那些内容不是“中医”的理性认识。
1701101349
1701101350
看来外来的东西一定要加以改造,且最好是不露痕迹才好流传。然而无论如何,印度眼科融入中医的历史,应该说还是以积极因素,即消化吸收、改造重建为主要表现形式。
1701101351
1701101352
9)菩提树下的蒙藏医学
1701101353
1701101354
阿输吠陀的风、胆、痰“三病素说”几乎被原封不动地“复制”到了中国的藏医学理论之中。通过下述有关藏医学中“三病素说”的介绍〔44〕,相信不仅可使我们了解两种医学体系间的密切关系,而且可以借助藏医学中的相关解释,进一步加深对“三病素说”的认识。
1701101355
1701101356
藏医认为:隆、赤巴、培根三大元素是构成人体的物质基础,也是进行生命活动所不可缺少的能量和基础。在正常生理状态下,三者在人体内保持着协调和平衡的关系,因而是生理性的。每当三者中的任何一个因素或几个因素由于某种原因而出现过于兴盛或衰微的情况时,则变成了病理性的东西,而出现隆的病态、赤巴的病态和培根的病态,在治疗上就需要对三者进行调整,使其恢复到原来的协调状态,达到健康的水平。
1701101357
1701101358
隆:是推动人体生命机能的动力,与生命活动的各种机能密切相关。它的机能与汉族中医的“气”很有些相似,但不完全一样。根据隆的不同机能与部位的不同,又可以把隆分成五种(与阿输吠陀“五风”的比较见表3.2)。
1701101359
1701101360


1701101361
1701101362
1701101363


1701101364
1701101365
1701101366
赤巴:具有火热的性质,也是负责人体内脏机能活动的一种因素,具有中医“火”行的性质。这是一种生理活动所需要的火或热量,与病理上的火邪不同。根据赤巴存在的部位和具体功能的不同,赤巴又可以分成五种(比较从略)。
1701101367
1701101368
培根:具有水和土的性质,与人体内津液、黏液及其他水液的物质和机能保持密切的关系。也有人把培根译成痰或黏液。这里的“痰”是正常生理状态下存在的正常物质,而不是病理状态下出现的痰液。根据其所在的位置及功能,又分为五种(比较从略)。
1701101369
1701101370
此外,藏医学认为人体有七种“基础物质”和“三种秽物”。七种物质为:食物精微、血液、肌肉、脂肪、骨骼、骨髓和精液;三种秽物为:粪便、尿液和汗液。实际上,这一说法同样也是来源于印度医学。
1701101371
1701101372
“从16世纪开始,藏医学典籍《四部医典》随藏传佛教,以寺庙教育的形式,广泛、系统全面地传入蒙古地区。从17世纪中叶,准噶尔学者蒙古人咱雅班智达·那木海扎木苏把《四部医典》从藏文译成蒙古文。并木刻出版。18世纪时,黄旗淖尔吉格西·敏珠尔道尔吉蒙译的清代北京木刻版本印行,成为蒙古医生的必读工具书。”〔45〕
1701101373
1701101374
而蒙医的“三根学说”以及将“三根”的“赫依、希拉、巴达干”各分为五,无疑就是藏医“隆、赤巴、培根”的拷贝,其源头自然可以追溯到印医的“三要素”。此外,蒙医的“七精华”(精微、血、肉、脂、骨、髓、精)、“三秽物”等也是一样,毋庸赘述。
1701101375
1701101376


1701101377
1701101378
1701101379
三、从“汉方”看中国医学在异域被接受、改造并创新
1701101380
1701101381
日本有称为“汉方”的传统医学。然“汉方”究属中国传统医学的复本,还是日本特有的传统医学呢?毫无疑问,“汉方”的母体是中国的传统医学知识,但与中国医学同源异流、同中有异的“汉方”,又是选择性吸收后加以改造的创新产物。《远眺皇汉医学》是我近年所写有关汉方医学史研究与介绍的一本小书,2007年由台湾东大图书出版公司出版。如有兴趣更多了解与研究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史,可以找来看看。以下所介绍的,即这本小书中涉及的一点点内容。
1701101382
17011013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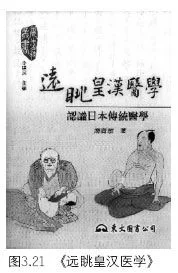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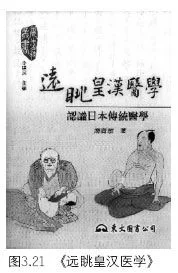
1701101384